

来源:文学报 | 麦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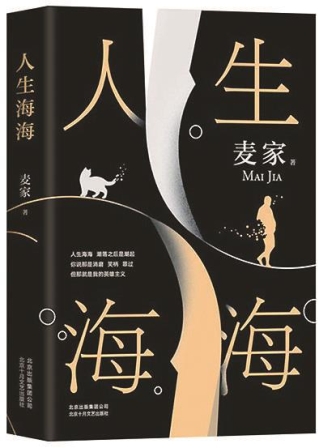
《人生海海》麦家/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
阔别八年后,麦家在长篇小说新作《人生海海》中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小说中,主人公“上校”也被称为太监,作为村里的一个传奇人物,他所讲述的故事、别人所经历与他相关的故事、别人讲述的他的故事相互交缠,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冲撞中,虚实相生,构成了无尽的叙事魔力。
1
我们村叫双家村,大家姓蒋,小家姓陆,大大小小五千多人,是全县排头尖的大村。因着人多,怪胎也少不了,老保长是一个,门耶稣是又一个,凤凰杨花是再一个。老保长怪的是,他有一双识别婊子的火眼金睛,什么女人守不住身子,他一看一个准,所以七十多岁,而且穷得叮当响,照样有人跟他轧姘头,因为他看准对方是个婊子,要淫荡。门耶稣怪的是,他把一个光着身子的西洋人当菩萨,供在家里,日日夜里对他跪拜,跟他诉苦,有时还对他哭,眼泪一把把流。凤凰杨花怪的是,她跟一百个男人睡觉也下不了一个蛋,因为她是只石鸡,比木鸡还要木。
当然最怪的人是太监,这不用讲,大家公认,看得见,摸得着。我觉得村里所有人的怪古加起来也顶不上太监一个人,他绝对是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,怪古的名目要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——
第一个,他当过国民党,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,是政府打倒的人,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。但群众一边斗争他,一边又巴结讨好他,谁家生什么事,村里出什么乱子,都会去找他商量。即使我爷爷,平时很讨厌他跟我父亲搅在一起,但只要家里遇到什么要紧事,照样要去请他拿主意,好像他才是真正的巫头,天下事都知晓。
第二个,他从前睡过老保长女人,照理是死对头,可老保长对他好得不得了。爷爷讲太监最后是被解放军镇压回来的,刚回村里时各种风言风语的罪名把他涂成一个恶鬼,狰狞得跟染上麻风病似的,即使父亲也一时不敢去贴他;大家都怕他,避他,奚落他,只有老保长一人张口“侄郎”闭口“侄子”地叫他,帮衬他,宣扬他,慢慢替他立起后来的威信。最该恨他的人却对他最好,这就是古怪。
第三个,他是太监,不管是怎么沦成太监的吧,反正是太监,那地方少了那东西。但每到夏天,大家都穿短脚裤的时候,我们小孩子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,好像还是满当当的,有模有样的。而且,好几次我看他在外面撒尿,照样像其他男人一样,脚站着,手把着,一点儿不像太监。据说,古代太监撒尿跟女人一样,是蹲着的。
第四个,他向来不出工,不干农活,不做手工(包括木工,他的老本行),不开店,不杀猪,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,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,嗑瓜子,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,抽大前门香烟,穿三接头皮鞋和华达呢中山装。更气人的是,他家灶屋好像公社食堂,经常飘出撩人的鱼香肉味。
第五个,他养猫的样子,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要操心,下功夫,花钞票,肉疼、宝贝得不得了,简直神经病!
2
村里无人不知晓,太监家有两只猫,一只全黑,一只全白,都跟小豹子一样,腰身长长的,头圆圆的,走路一脚是一脚,慢腾腾,雅致得很。我经常看见他用香皂给猫洗澡,用长柄木梳给它们梳毛,从头梳到脚,用金子小剪刀给它们剪趾甲,剪完又用砂纸磨。最气人的是,还专门给它们买上好的鲞吃!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,我吃过的鲞还没有他家猫多。
我宁愿做他家的猫。我敢说,这也是我身边所有小孩子的想法。
表哥说,他还跟猫一起睡觉。但表哥也承认,只是听人说,没有亲眼见过。我倒是亲眼见过他跟猫讲话,而且猫好像也听得懂他讲的话。那年我才五岁,父亲给我三分钱,叫我去跷脚阿太开的小店买香烟。父亲告知我,三分钱可以买八支半前进牌香烟,如果他给我九支,我要对他鞠一个躬,叫一声“七阿太”;如果只给八支就不理他,甚至可以骂他跷脚佬,反正他是跷脚,追不上我。
跷脚阿太的小店开在祠堂门前,太监家在祠堂背后,我去小店必须经过他家门口。跟大多数人家不一样,他家有围墙,围着一个小院子——爷爷讲是以前的猪圈改造的,猪圈里放过毒炮弹壳。院门平时间不开,因为怕狗欺负他家的猫,那天却开着,我看见院子里有一畦菜地,种着香葱和芹菜,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拎着一只洋铁桶在给菜地浇水,太监自己则像个老爷一样,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,享着太阳,抽着香烟,看着报纸,脚跟边躺着一白一黑两只猫。
3
白猫最先发现我,对我昂头咪地叫一声,好像在通知主人,有人在门口。太监听了,放下报纸,抬起头,看见我。看了两眼,笑了,问我是不是老巫头的孙子。我摇头——那时我还不知道爷爷的绰号呢。
他母亲笑道:“怎么可能不是,简直跟他爹生一个模样。”
他哈哈大笑,扮着我爷爷的样子和口气招呼我:“哎,我的乖乖,进来吧。”
我看着两只虎视眈眈的猫,不敢进门。
他对它们一挥手,发命令:“你们进去。”
两只猫完全是听懂的样子,甩甩尾巴,立起身,对我龇一下牙,掉转身,一前一后,往黑暗的屋子里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阳光那么白亮,台地上明晃晃的,连太监手上的烟在冒气我都看得清明,可几步之后的屋子里,却是那么一团黑,一片黑,像被阳光抹黑似的。五岁的我不知道这是自然现象,以为这是鬼屋的现象,又想到刚才猫对我龇牙,好像要吃我,吓得我拔腿就跑。
事后我跟爷爷讲起这事,爷爷一把搂住我,兴高采烈又满怀感激地对我讲:“啊哟,我的乖乖,你不进去是对的,以后也不要去,那就是个鬼屋,那家伙就是个鬼。”
我嚷嚷:“他跟猫说话,还跟猫睡觉。”
爷爷讲:“所以他不是人,是鬼,鬼投胎的。”
以后好几年,我去小店买东西或去祠堂玩,都不从他家门口走。我宁愿绕一个大圈也不走他家门口,因为我怕遇到鬼。表哥说他家的两只猫是鬼变的,我说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也是鬼变的;表哥说鬼已经把他爹吃掉了,我说可能就是那死老太婆吃的。我们经常这样数落太监和他老母亲,我和表哥的友谊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牢固,好像我们有一个共同敌人,我们必须团结一起,不弃不离。
有一天,我和表哥正在这么乱讲太监时,被正在茅坑里解手的父亲听到。父亲从茅坑里出来,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追着我们骂,恼羞成怒的样子,好像太监是他亲爹,我们是茅坑里的臭石头。
表哥问我:“舅舅为什么对太监那么好?”
我想都没想,脱口而出:“因为他鬼附身了。”好似我早备好答案,其实是爷爷的话。
确实,爷爷经常骂父亲被鬼魔附身,给死人摸过额头。爷爷讲,运气是阳气,鬼魔是阴气,阴阳是相克的,甘苦是作对的,人一旦阴盛阳衰,苦头当道,就要倒霉头,背祸水,吃水也要呛死。据说以前父亲蛮听从爷爷的,父子俩像兄弟一样亲,我们家像谷仓一样让人羡慕,老小和睦,儿女顺当,人畜兴旺。但自从太监回到村里后,父亲老是淘爷爷的气,家里老是吵吵闹闹,搞得爷爷老是担惊受怕,怕霉运随时落到我家。